
陆炜
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
内分泌遗传代谢科
副主任医师
医学博士,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副主任医师。
先后赴美国Baylor医学院分子与人类遗传系、美国Boston儿童医院遗传系及内分泌科进修学习。
现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委员,中国医师协会青春期健康与医学专业委员会内分泌学组委员,上海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委员。
擅长儿童常见内分泌疾病、内分泌遗传综合征及遗传代谢性疾病的诊治。
性早熟的危害不可忽视
近十年来,世界范围内青春期发育开始的年龄有逐渐提前的趋势。同时,CPP 的诊断与治疗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。CPP 发病率约为 1/5,000~1/10,000,女童发病率为男童的 5~10 倍[1]。同时,CPP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,如韩国 CPP 女童发病率从 2004 年的 3.3/10 万上升到 2010 年的 50.4/10 万,男童从 0.3/10 万上升到 1.2/10 万[2]。
2014 年,在我国北京、上海等 10 个省市开展的一项儿童性早熟现状调研显示,我国性早熟患儿以女童为主,男女比例约为 1:16,初次诊断为 CPP 的患儿高达 88.91%。我国性早熟患儿初次诊断为 CPP 的年龄为(8.35 ± 1.57)岁,骨龄为(10.11 ± 1.70)岁,骨龄比实际年龄平均提前 1.65 岁[3]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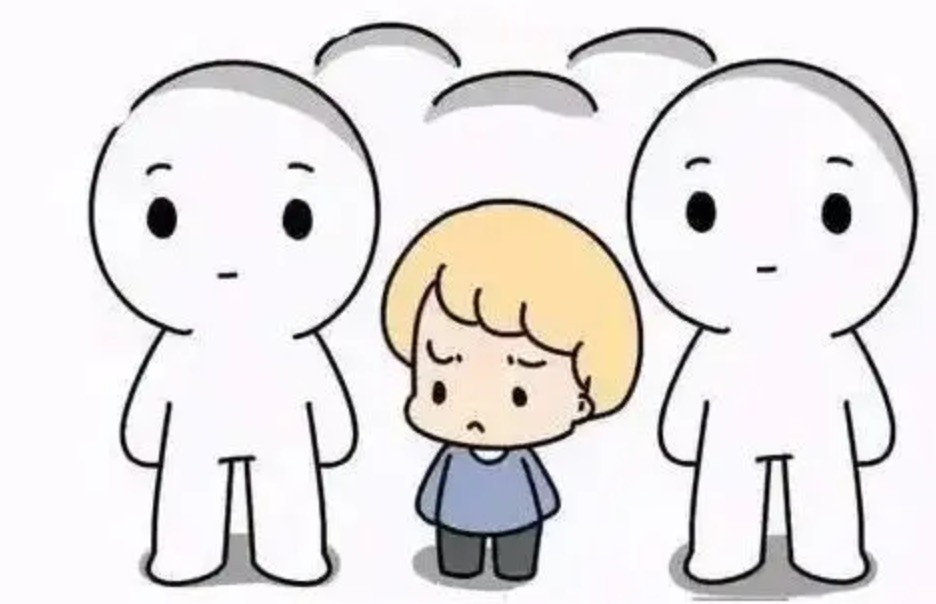
CPP 对身高、体重、性发育、心理健康的危害不容小觑
CPP 儿童提前进入青春期,骨骼发育加速,导致骨骺过早闭合,生长时间缩短,从而影响患儿成年后的终身高。性早熟引起平均终身高损失具有性别差异,女孩成年后终身高约为 152 cm,平均损失约 10 cm;男孩成年后终身高约为 156 cm,平均损失约 20 cm[4]。CPP 对儿童的身高影响与发病年龄、骨龄超前程度、性激素水平和体质指数(BMI)密切相关[5]。缓慢进展型 CPP 骨骼生长速率缓慢,对儿童身高的影响不大;快速进展型 CPP 骨成熟加速,生长潜力明显缩短,对身高的影响更为明显[6]。
肥胖是 CPP 的危险因素之一,CPP 和肥胖两者存在共同的神经内分泌调节。有研究显示,13.86% 的性早熟女孩存在肥胖,其中 29.42% 为中心性肥胖;25.98% 的性早熟男孩存在肥胖,其中 38.58% 为中心性肥胖[7]。
CPP 是引起儿童性发育异常最常见的疾病之一。CPP 患儿的发育规律与正常青春期儿童一致,但性发育时间较短,内生殖器官的发育可能较不成熟,容积也较小[8],可导致一系列问题。如特发性 CPP 女孩患「多囊卵巢综合征」的几率增加,可能与特发性 CPP 患儿体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、胰岛素水平增高等一系列内分泌环境改变相关[9];月经初潮过早出现也会增加乳房肿瘤的风险[10]。
由于第二性征过早发育,患儿可能会产生一系列心理问题或社会行为异常。流行病学研究表明,早发育更易引起功能性表现(如胃痛、头痛、关节痛等)、抑郁症状、性接触等心理行为问题。女孩易出现酗酒、超重、性行为,男孩则更易出现吸毒等冒险或犯罪等品行问题[1]。性早熟患儿出现焦虑情绪、躯体化/惊恐、广泛性焦虑、社交恐怖和学校恐怖的比例显著高于健康儿童,而长期过度的焦虑情绪可降低生理及社会功能,演变为情绪障碍。同时,性早熟患儿的自我意识发展普遍落后于健康儿童,表现为自我意识总分、行为、躯体外貌与属性、焦虑、合群、幸福与满足显著低于健康儿童[11]。

CPP 的发病机制和遗传因素
CPP 的发病机制涉及到一个重要器官——下丘脑。下丘脑是调节内脏活动和内分泌活动的较高级神经中枢所在。它如同一个开关,掌控着人体生长发育的每个进程。如果下丘脑提前分泌和释放 GnRH,就相当于提前激活了性腺轴,导致性腺发育和分泌性激素,呈现出内、外生殖器发育等体征[1]。
相关因素分析发现遗传、肥胖、环境内分泌干扰物以及心理、营养等相关因素与儿童性早熟密切相关。基因组学研究发现 DLK1、MKRN3 基因缺陷均与性早熟密切相关[12,13]。
首次发现 CPP 具有遗传倾向的研究,发表于 2013 年的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。该研究发现与 CPP 有关的父系表达印记基因 Makorin 环指蛋白 3(MKRN3)。5 个家族性 CPP 患者中发现了 4 个 MKRN3 基因突变,且均为父系遗传[13]。另一项研究发现 MKRN3 水平与 BMI、黄体生成素(LH)、促卵泡激素(FSH)、女性雌二醇(E2)呈负相关。当 MKRN3 未突变时,CPP 患儿 MKRN3 水平与青春期匹配的人群相近[14]。
DLK1 基因也与性早熟相关。一项研究对 5 名有 CPP 女性的家庭进行连锁分析和全基因组测序,结果提示所有患者血清 DLK1 均检测不到(< 0.4 ng/mL),支持因基因缺陷导致患者完全无 DLK1 产生。此家族中发现了一个复杂的 DLK1 缺陷;DLK1 为父系表达的印迹基因,即只有从父亲遗传了这种缺陷的家庭成员才会出现性早熟[12]。
肥胖(中心性肥胖)与儿童青春期早发育呈正相关,BMI 与女童性早熟具有相关性[7,15]。干扰内分泌的化学物质不仅会影响青春期发育,还会影响性别认同、内外生殖器的发育、新陈代谢和神经认知发育[15]。

CPP 的分类及病因
CPP 根据病因可分为特发性 CPP 和继发性 CPP。后者常继发于中枢神经系统异常或其他疾病。《中枢性性早熟诊断与治疗共识(2015)》明确指出[1]:小于 6 岁的 CPP 女孩以及所有男性性早熟患儿均应常规行头颅 MRI 检查。小于 6 岁的 CPP 女孩,中枢神经系统异常比例约占 20% ,且年龄越小,影像学异常可能性越大;6~8 岁的 CPP 女孩是否均需行头颅 MRI 检查尚有争议,但对有神经系统表现或快速进展型的患儿则应行头颅 MRI 检查。男性性早熟虽然发病率相对较低,但 25%~90% 的患儿具有器质性原因,约 2/3 的患儿有神经系统异常,50% 左右的患儿存在中枢神经系统肿瘤。临床诊断明确后应进行 CPP 病因诊断,根据病情进行头颅 MRI 检查、肾上腺功能、甲状腺功能等评估,以了解是否存在中枢神经系统病变或其他疾病。
在 CPP 的诊断过程中,还应注意明确性早熟是否继发于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、多发性骨纤维发育不良、家族性男性限性性早熟、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等,临床中应加以区别和分析[1]。
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:多为 21-羟化酶缺乏,可导致男孩外周性性早熟。表现为阴茎增大、增粗,阴囊色素沉着,睾丸容积不大或睾丸容积与阴茎发育水平不一致。早期身高增长加速,骨龄提前显著。临床要结合血 17-羟孕酮、硫酸脱氢表雄酮、雄烯二酮、睾酮水平综合分析。值得注意的是,此病长期未经诊断治疗者可转变为 CPP[1]。
McCune-Albright 综合征,又称多发性骨纤维发育不良:常因 Gs 基因缺陷所致,女童多见。以性早熟、皮肤咖啡斑、多发性骨纤维发育不良三联征为特点。多数患儿仅表现一种或两种体征,可伴有垂体、甲状腺和肾上腺等内分泌异常,还可出现卵巢单侧囊肿。但其性发育过程与 CPP 不同,常先有阴道出血发生,乳头、乳晕着色深等。常发现血雌激素水平增高而促性腺激素水平低下,GnRH 激发试验呈外周性性早熟。此病可部分转化为 CPP[1]。
家族性男性限性性早熟:由于 LH 受体激活突变所致,呈家族性特点。患儿 2~3 岁时常出现睾丸增大,睾酮水平明显增高,骨龄明显增速,但 LH 对 GnRH 刺激无反应。此病也可随病程进展转变为 CPP[1]。
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:常与继发 CPP 和下丘脑-垂体-性腺轴的调节紊乱有关。甲低时,下丘脑分泌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(TRH) 增加,由于分泌促甲状腺激素(TSH)的细胞与分泌泌乳素(PRL)、LH、FSH 的细胞具有同源性,TRH 不仅促进垂体分泌 TSH 增多,同时也促进 PRL 和 LH、FSH 分泌。该病常伴有性早熟的表现,如女孩出现乳房增大、泌乳和阴道出血等,但不伴有线性生长加速及骨龄增长加快。病情严重而长期未经治疗者可转变为 CPP[1]。
总结
近年来,在世界范围内,儿童 CPP 发病率均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,且发病年龄有所提前。我国性早熟儿童中绝大多数为 CPP。由于生长发育加速,骨骺提前闭合,导致 CPP 患儿成年终身高受损、肥胖、性发育异常等,严重威胁儿童身心健康,导致一些心理和社会行为问题。CPP 的发病机制与下丘脑提前分泌和释放 GnRH 有关,与遗传、肥胖、环境内分泌干扰物以及心理、营养等因素密切相关。CPP 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,目前已知与 MKRN3 基因和 DLK1 基因缺陷相关。临床中,CPP 可分为特发性和继发性两种病因分类。在诊断 CPP 时,应注意排除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等其他继发性疾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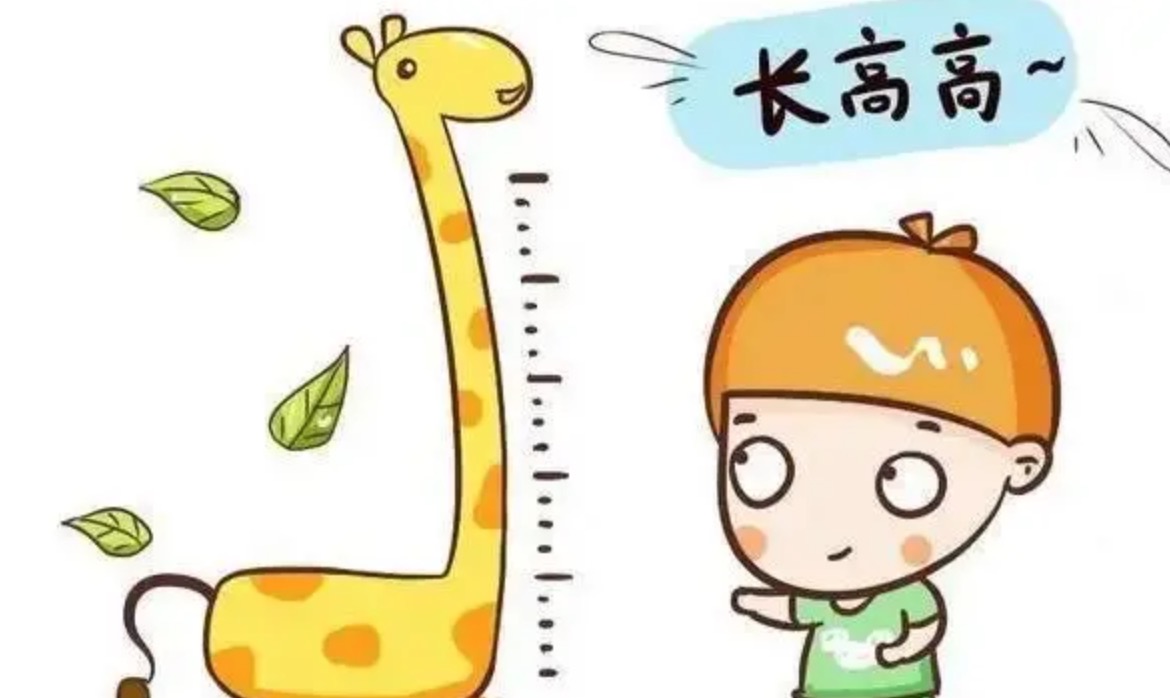
本文为中立科普内容,不涉及任何商品推广。文中所介绍的治疗方案有明确适应证,需要确诊后在医生指导下使用。如想采用该治疗,请到正规医院就诊,遵医嘱治疗。
科普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平台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海纳患教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